動力美學-波丘尼的未來主義繪畫與雕塑
In Praise of Kinetics: The Futurist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of Umberto Boccioni
作者: 楊衍畇(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博士)
Yang Yen-Yun (Ph.D. in Arts, Taiwan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R.O.C.)
未來主義藝術的實踐家波丘尼( Umberto Boccioni)在三十四歲的短暫生命中,創作出許多未來主義代表性的傑作,未來主義創始人馬里內提( F. T. Marinetti, 1876-1944) 提出速度及運動才能表現這個時代精神,而波丘尼在繪畫上運用了力線(force-line),城市街景、人際關係、都市文明,全世界在他的筆下狂亂地動了起來;力線亦擴展至雕塑的造形語言中,強調四度空間的表現,從傳統雕塑僅著重在客體本身的三度空間表現, 轉變成強調客體必須與環境做結合的現代雕塑。本文將藉波丘尼的代表作品,解析他的造形語言及創作意涵,進一步了解他的動力美學。
本文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都市化與工業化的文明腳步漸行加劇,火車、電話、電燈等科技發明將人類的視野帶向另一嶄新的想像空間。當汽車一問世,極致的速度感刺激了人類的感官,世界不再是靜止的,透視不再是三度的,空間隨速度在改變,四度空間增加了我們生命的不確定性、可變性。對於急欲使有著歷史光榮包袱而停滯不前的義大利向前邁進的愛國之士,這變動的現象是有積極的面向。二十世紀初,儘管義大利經過復興運動( Risorgimento )的努力,1861年由地方分權轉變成一統的民族國家,但在文化上仍是沉浸於過去古羅馬、文藝復興的古典美感中,與當時國際間所盛行法國的立體主義有所脫節。
1909年2月20日,詩人馬里內提( F. T. Marinetti) 首先於法國費加洛報(Figaro) 提出「未來主義宣言」,成為未來主義的思想綱領,最初實現於詩與文學的領域。宣言中表示他驚艷於汽車的速度美感,甚至認為勝過於古典雕塑,曾說道: 「這個世界由一種新的美感便得更加光輝壯麗,這種美是速度的美。…如機關槍一樣風馳電掣的汽車,比帶翅膀的薩莫色雷斯( Victory of Samothrace)的勝利女神像更美。」意即義大利的未來文化光榮必須與過去的歷史斷絕,現代文明所產生的速度美感才是能提升國家文藝的方法。正如法國思想家傅柯所認為,歷史之間彼此是沒有關係的,是斷裂的狀態。宣言一產生,義大利有許多藝術家都躍躍欲試,最具代表且最成功的就屬波丘尼( Umberto Boccioni, 1882-1916)。1910年2月11日,波丘尼號召了卡拉( Carlo Carra, 1881-1966)、巴拉( G.iacomo Balla, 1871-1958)、塞維里尼(Gino Severini, 1883-1966)、盧梭羅(Luigi Russolo,1885-1947)等藝術家,發表「未來主義繪畫宣言」,又於同年4月11日提出「未來主義繪畫技術宣言」,在視覺藝術中實踐馬氏的宣言的理念,尋找詮釋動力的造形語言,題材上則以表現都市生活、機械與速度為主。他們致力表現的是「現代生活的漩渦-一種鋼鐵的、狂熱的、驕傲的、疾馳的生活。」[1]不同於當時國際藝壇所盛行的立體主義展示機械的靜態美,行動派的未來主義畫家則在畫布上詮釋運動、速度和變化過程。

圖1: 城市的興起
圖1: 城市的興起
在未來主義的藝術圈中,波丘尼可說是文武雙全,他不但能將馬里內提的宣言精神發揮於繪畫及雕塑中,更能提出新的造形想法成為理論。並且是唯一傑出的未來主義雕塑家。尤其是他提出雕塑的材質不限於傳統的石材、木材等,擴展至玻璃、水泥、鋼鐵、硬紙板,甚至髮毛、鏡子、布料等實物,雖然以上新式材料並未在他的作品中出現過,但在後来的達達主義和構成主義中實現。波丘尼早年學於巴拉( Giacomo Balla) ,受到巴拉分離派的色彩影響,運用細碎的顏料色彩堆疊成明顯的筆觸。自1910年起受表現主義影響,,透過極具張力的色彩呈現扭曲人物造形,從此波丘尼常擺蕩在印象主義的色彩研究與表現主義的光線與造形問題之間。1910年的<城市的興起>(The City Rising; 圖 1)是波丘尼首幅將光、色彩與運動結合成一體的表現,將運動詮釋成巨大力量的漩渦,企圖追求「勞動、光線和運動的偉大综合」[2]。畫面前景是一匹巨大的红色奔馬,充满活力,揚蹄前進;馬的前方,扭曲的人物如骨牌效應般纷纷倒下,而背景是正在興起的工業建設。整幅畫充滿了象徵的寓意性:巨馬暗指未来主義者所迷戀的現代工業文明,它正以勢不可擋之態猛烈迅速地發展,而人群則暗示勞動的活力。波丘尼在此以短促碎裂的筆法塑造運動中的馬匹,群眾拉扯的力量,及工業城市中的旺盛生產力,由色彩形成光線從畫布中放射出來,將速度,光線與色彩交融在一起。

圖2: 心靈狀態:告別
圖3: 心靈狀態:離開之人
圖4: 心靈狀態:;留下之人
未來主義是在義大利米蘭發起的,馬里內提認為具現代美感的未來主義應該擴展至國際間,急欲取代國際藝壇中的主流-立體主義,於是早在1910年起在世界各地安排展覽與演講,包括巴黎、倫敦、柏林及莫斯科等地。而波丘尼亦與卡拉於1911年自行前往巴黎調查當時的藝術氛圍,了解畢卡索與布拉克的立體主義美學,波丘尼拜訪了法國詩人及藝評家阿波里內爾( Guillaume Appolinaire)並呈現新作 <心靈狀態> ( State of Mind,1911年; 圖2-4) 給他看,<心靈狀態>為三聯畫作, 包括<告別>(圖2)、<離開之人>(圖3)、<留下之人> (圖4)。若說<城市的興起>描繪了外在世界的變動性,<心靈狀態>則是將人的內心情緒與外在世界對話。<告别>描繪著水洩不通的車站場景,左右側各有一組情侶相擁告別,但有可能是同一對情侶,綠色的身形呈現出他們依依不捨的悲傷情緒。由右而左,由上而下地穿越畫面中央的火車與情侶佔據了整個畫面。畫面上,力線(force-lines)和色彩相互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系列重疊綿延的造形组合。在極度壓縮的空間裏,曲線和直線穿插交錯,塊面與塊面擠壓移位,形成分散與聚合、斷續與重複的節奏,帶给觀眾不安的壓抑感。畫面的中央是幾個非常工整的數字,浮現在解體的火車車廂上,在嘈雜紛亂的畫面中,表現另一種意外的冷靜和理智。這些數字使我們聯想起布拉克和畢卡索有着文字和數字的分析立體主義作品。<離開之人>以向左的斜線呈現火車行進的速度感,顏色則延續<告別>清一色的綠表達遠行者的寂寞之情,背景則著窗外的黃色屋舍,旅客背對著窗景閉眼沉思,似乎一切外物與他無關,心繫家鄉故人。因速度作用使不同時間點的人物面容統一在畫面同時呈現,因心境的焦慮使旅客的容貌扭曲變形,<留下之人>的畫面則一致採灰綠的單色,滿佈的垂直線強調送行人的沮喪,好似傷心地要自人間蒸發掉, 勉強拖著沉重的步履蹣跚地向右前方行進。儘管這三幅作品的標題有敘事的暗示,但畫家真正的意圖是藉著離別主題所產生內在情緒的動力詮釋真實造形元素的構成。
表面上,波丘尼的作品看似有立體主義的特質,實際上他並沒將形式要素重構, 波丘尼著重色彩的互補特性及客體與所處環境的關係。波丘尼曾批評立體主義: 「他們固執地繼續描繪事物不動、凍結、靜態的本質… 這樣的畫法是荒謬的,是心智懦弱的行為,甚至就像以線性、球狀、立體的造型詮釋客體。借用寓言意義於日常的裸體中,將繪畫的意義由客體本身或是從其周邊有關的一切去除,對我們的心靈來說是傳統及學院的心態。」同時更表示「為使觀者活在繪畫的中央, 如我們在宣言中所表示,繪畫必須是人所記得、所看到的一切綜合。」[3] 因此,波丘尼主張以力線來綜合所經歷過的一切,無論是肉眼所看到的外在物質面,或是心眼所透視的內在精神面,透過力線(force-lines)會使面相互交錯滲透。他曾形容:「假如我們描繪暴動的層面,根據畫面的暴力法則,群眾揮舞著拳頭,警察嘈雜的攻擊以線束詮釋衝突的力量。這些力線必定圍繞著不得不與畫中人物一起掙扎的觀者,所有的客體配合著物理先驗論(physical Transcendentalism),藉由我們直覺所感知持續的力線向無盡延伸。若我們要將藝術品回歸到真正的繪畫,我們就要畫這些力線。我們在畫布上藉著線條詮釋本質,因為客體將韻律的開始或延長印在我們的感知上。」[4]

圖5: 笑
波丘尼成功地以力線捕捉到離別哀愁的<心靈狀態>,在<笑>(Laught, ;圖5)一作中卻帶著一抹嘲諷滑稽,儘管畫面左上方的戴帽女郎開懷大笑,右方顏面模糊的男子似乎談笑風生、暢飲不斷,咖啡廳內的嘈雜歡樂氣氛為多道光束所加強, 但他們的儀態仍像在演舞台劇般戲劇性。波丘尼受到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 「笑論」(Treatise on Laughter)及留下記憶影象的理論影響,柏格森形容笑的機械作用就如「理性建構系統突然轉譯成旋轉的機器」,笑的網絡放射出交織的物體與空間、背景與前景。[5] 機械裝置的規律性,本就與人性的多變性相抵觸,未來主義後期的藝術家朝向機械人概念發展(尤其以戲劇,舞蹈與電影為多),機械化的造形與動作總令觀眾發笑,而這種笑的情緒帶著一股淡淡的悲愁。
繪畫上執著於四度空間的研究,波丘尼自1912年起將創作的領域拓展至三度空間的雕塑上。對過去的雕塑,尤其是埃及希臘的形式與米開朗基羅的宏偉性,他嗤之為「怪物般的時代錯誤」[6]。儘管在二十世紀初有雕塑家如羅丹( Auguste Rodin, 1840-1917)、莫尼耶(Constantin Meunier, 1831-1905)、布荷戴爾(Emile-Antoine Bourdelle, 1861-1929)等致力於造形語彙上改革,但觀念上仍固守於三度空間的表現。僅有羅梭(Rosso Medardo, 1858-1928)被波丘尼視為天才型的雕塑家。因為他企圖以印象派式地臘塑來革新傳統的造形,將環境與氛圍與三度空間連結,為雕塑開創更廣闊的創作領域。但波丘尼認為羅梭的努力有所侷限,因為形象仍認知為「世界在其自身中」。[7]若羅梭運用光影交錯雕琢物象本身為單一獨立的塊體,波丘尼則將影像分解重組成具結構性的物件-透過光線切面成造形表面,使雕塑與環境共生共存,將無生命內在的動力釋放出來。1912年4月11日,波丘尼所發表「未來主義雕塑技術宣言」,就是要顛覆傳統的雕塑語彙,以新的形式塑造現代雕塑,提出「平面的交互穿透」(compenetraion of planes)的論點:「要將可見造形的無限性與內在的造形無限性不可見但數學地連結在一起。因此那新造形藝術將會把與事物連結交會的空間平面轉化成灰泥、青銅、木材、及其他想要的材料。」意即「有限與雕塑之絕對及完全的毀滅在自身完成。」 [8] 之後,他又更清楚說明穿透的概念:「未來主義的雕塑構圖包含形成當代物體的美妙數學與幾何元素。這些物體將不會用來作為雕塑解釋性的屬性或分離的裝飾性元素,而是符合新的和諧概念法則,於人體的肌肉線條中體現。因此某件機械的輪子可以自機械師的腋下伸出;桌子的線條可以穿透正在閱讀的人之頭部,書頁亦能切開讀者的胃部。」[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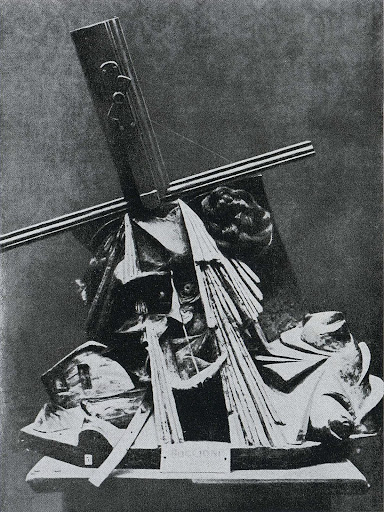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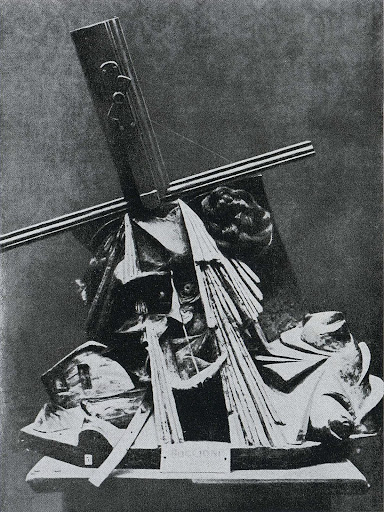
圖6: 頭部與窗戶的融合
圖7:反優雅
圖8: 水平量感
1912-1913年的實驗階段中,波丘尼提出的穿透概念造形上無法很明晰的表現出來,或是仍受到羅梭印象派的明暗效果影響。 1912年的<頭部與窗戶的融合>( Fusion of a Head and a Window;圖6),波丘尼大量使用不同的材質(如玻璃眼球、頭髮、取自支撐器的橫木等實物)使物體透明,或是過分強調物體與空間的作用,所有的物體-窗戶的橫木、人頭、力線形成的光束、房舍等全都凝結成怪物般的龐然大物,巴洛克的詮釋喪失了他所強調的動力美感。[10] 1913年<反優美>(Antigraceful;圖7)仍擺脫不了羅梭的影響,人物臉部的肌肉呈凹凸的塊狀,藝術家以光影的明暗變化統一流動,瞬間的意象,企圖建立起自己的風格。類似<反優美>的雕塑作品,繪畫上則有1912年的<水平量感>(Horizontal Volumes;圖8),波丘尼純熟地運用力線將人物的儀態表情及所在環境的情狀深刻體現,力線在平面作品中總能將客體與環境成功地綜合起來,線本身就屬於平面的一部分,而三度空間的雕塑要表現力線,力線本身就會變身成為三度,增加統合的困難度。

圖9: 瓶子在空間的發展
圖10: 空間持續性的獨特形式
經過不斷地努力嘗試,波丘尼終於解決動力與空間在雕塑中的造形問題,於1913年完成了<瓶子在空間的發展>(Development of a Bottle in Space;圖9),以及他最成功的雕塑作品<空間持續性的獨特形式> (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圖10)<瓶子在空間的發展>中,雕刻家波丘尼找到以螺旋狀延展瓶子的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這內外空間不再受限於玻璃物質而能彼此進行對話。對藝術家而言,螺旋狀是表現「於宇宙動力之中形狀延續性」的原始形體,指示著持續律動的演化,這意謂立體主義的分割已無法捕捉事物命的過程。波丘尼肯定地表示「力形(force-form)源於實際的形式」[11],暴露出來內在空間的瓶子強調非物質性,螺旋狀的結構使它具有如紀念碑式的宏偉性。<空間持續性的獨特形式>則是表現行走中的人,健步如飛的腳步,風速及體內的爆發力改變了人的形體,波丘尼同樣以螺旋狀的弧形表現人體肌肉的變化,強調人與速度同在的共時性。身體在運動的歷程中延長,構圖簡化而明晰,成功地達到客體與環境間掙扎的綜合。
1914年,波丘尼的雕塑作品充滿了生命力及鮮活的色彩,更深層地解決空間問題,空間不再是一個呈現與周遭真實關係的向度,絕對運動及相對運動為客體固有的動感性質。如波丘尼所寫道:「客體的造形潛在性在於它的力量,意即原初的心理學,使我們能在畫面中創造不以敘事重現事件的新題材,而是協調真實的造形價值,協調純粹結構性,避免文學或情感的影響。在我所解釋如某物分離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的運動最初狀態中,客體在相對運動中看不見,而能根據其力量的傾向於所解構的活躍線條感知到。因此我們到達不再存於立體派模式的客體解構,而是客體本身的面貌,藉由超越於舊藝術的無限精練感覺來詮釋。」[12] 避免文學敘事,回歸一切事物本質的抽象觀念,是現代藝術家所主張的創作方向,亦是波丘尼能成功結合事物精神與物質的面向,展現四度空間的無限性。然而, 1914年末至1916年不幸墬馬身亡,波丘尼退回後印象派,尋求塞尚所強調的量感,詮釋物體的深度、寬度、及高度,或許是因為大戰爆發影響他的創作風格,又因加入義大利國民軍而使他作品相對減少。波丘尼這顆未來主義的明星,並不會隨著他的殞落而失去藝術上的光彩,他在繪畫與雕塑上的現代觀念仍為當代藝術家所應用。
結語
對波丘尼來說,人的價值是以動力來定義的,有行動力的人才能邁向更有希望的美麗未來。波丘尼本人就有充沛的行動力,他做任何事都能極為有效率的達成目標:他將後印象主義的色彩及表現主義的造形,光線融會於他的未來主義繪畫的都會題材中,以力線來連結物質與精神兩個世界;在雕塑上則強調客體與環境的綜合性,將造形語言拓展到四度空間,甚至多度空間的可能性。文明的速度震撼了人類的官能,而人類的思想就如我們所處的空間隨時變化,波丘尼感觸到柏格森所提出的「生命衝動」( élan vital) : 「如塵土旋轉,擲於拂過的微風中,活著的事物自轉著,被生命偉大的氣息承載。」[13] 為充分展現生命力,在無機體中是要透過自身的造形延展出來,而對有機體來說,是要與動力與環境融為一體。宇宙的存在是因為人類的行動,人類的價值是在於和宇宙一同運行。
參考書目
1. Caroline Tisdall & Angelo Bozzolla, Futu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 Herbert Read, Modern Sculpture, Thames and Hudson,1985
3. Estern Coen, Boccioni,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Y. 1988
4. A.M. Hammacher ,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culptur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 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88
5. Richard Hertz & Norman M. Klein eds., Twentieth Century Art Theory. Urbanism,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0
6. Giovanni Lista, Futurism, Terrail, Paris.2001
7. Renato Poggioli著,張心龍譯, <前衛藝術的理論>, 遠流出版社,1992年
[1]雷蒙·柯尼亞等著,徐慶平等譯:《现代繪畫辭典》,人民美術出版社,第30页
[2] 同上
[3] Estern Coen, Boccioni,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Y. 1988 , p.25
[4] Ibid, p.26
[5] Caroline Tisdall & Angelo Bozzolla, Futu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41
[6] Estern Coen, Boccioni,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Y. 1988 ,p.205
[7] Ibid, p.206
[8] Ibid,p.27
[9] Ibid. p.206
[10] 除<反優美>,<瓶子在空間的發展>,<空間持續性的獨特形式>三件作品留存下來,波丘尼其他雕塑作品則在1916年米蘭展中破壞殆盡.
[11] Giovanni Lista, Futurism, Terrail, Paris.2001, p.87
[12] Estern Coen, Boccioni,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Y. 1988 pp.32-33
[13] Caroline Tisdall & Angelo Bozzolla, Futu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50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